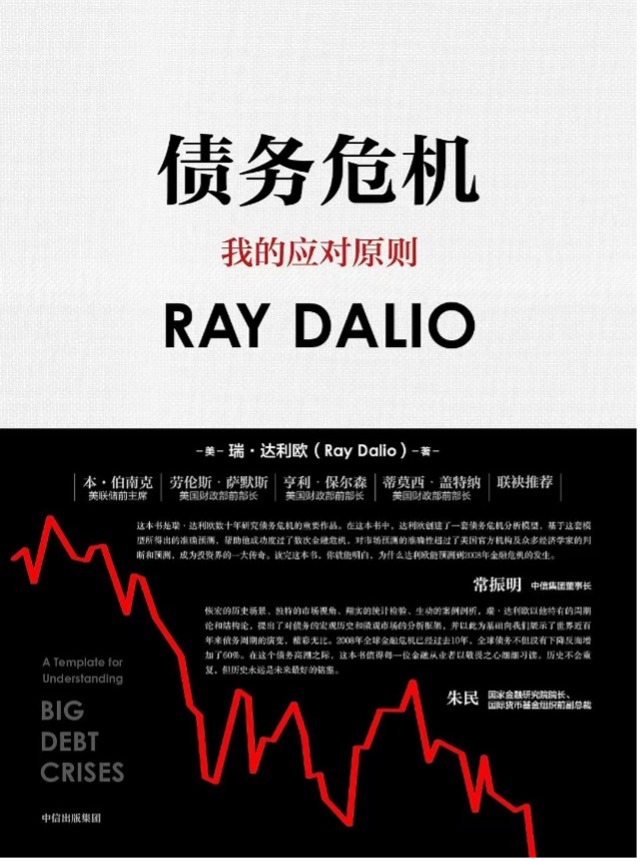过去几十年来,房地产泡沫的累计与破裂往往推动着一个经济周期的开始与结束。写下这篇文章的初衷,旨在以相对简单易懂的方式,将瑞·达利欧(Ray Dalio)的《债务危机》书[1]中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案例分析和他本人提出的债务周期概念做一个回顾与总结。这部分内容包括:次贷危机中的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对贝尔斯登的救助以及雷曼兄弟的破产等主要金融事件。在此之上,文章对美国政府在救市过程中所面临的大量政治困境与挑战,等次贷危机中易被忽视但却扮演重要角色的非经济因素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与讨论。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救助大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及其争议,和对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讨论上,引用的材料包括了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的口述回忆[2]和《新自由主义与银行救助》[3]这篇论文里的部分内容。
2001-2007: 泡沫中的集体癫狂
“债务泡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债务增速远远超过了收入增速”[1:1]
在达利欧的理论中,债务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其前提条件是债务的创造可以带来足够经济效益,以确保债务本身可以得到偿还。在现实世界里,债务推动的经济不会永远保持增长,反而呈现周期性的特点。 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债务周期的崩溃所导致的,而次贷危机在达利欧的理论框架中就属于“典型通缩性债务周期”的产物[1:2],运用该框架,作者在书中对次贷危机中泡沫的累积与破灭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宏观背景
为什么美国的居民和企业债务(不仅限于房地产)在次贷危机前会持续高速增长?一个主要原因是,宏观环境上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1年,为了缓解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所带来的经济衰退,美联储持续降低利率,将其维持在1%左右,而极低的融资成本刺激了家庭部门的支出和借贷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市场对地产价格长期上涨的预期,极大地刺激了房地产投资。
反常识的循环
这种预期并非凭空而来的大饼,而是有着丰富的历史数据来支持——房价在过去几十年内的持续增长。对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叠加基于此预期下注的贷款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循环:借款人愿意借更多的钱,因为购买房产的净值增速远远超过借款的成本,而因为房产作为抵押品持续升值也让银行看不到贷款违约的风险,贷款人也更愿意发放贷款。这种循环如此演变,带来了一种和正常逻辑相反的结果:发的贷款越多,信贷标准反而越低。反映到现实的直接现象就是,在次贷危机发生前的6年里,债务增幅最大的是没有足够偿付能力,收入位于最底层五分之一的借款人[1:3],并且与之密切相关的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占据了20%的市场份额[1:4]。在房地产相关债务也野蛮生长的同时,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所依赖的几个关键指标(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一片向好,而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债务泡沫却被平均值所覆盖,宽松的货币政策得以延续,这又给泡沫的蔓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有了对债务泡沫背景的了解,我们将看到的是,各种金融工具是如何将杠杆一步步加大并把不良贷款的影响推向灾难。
螺旋上升的泡沫:金融创新
上文提到,房产的上涨间接导致了信贷标准的降低:因为房子一直在增值,银行并不怕自己发出去的贷款会违约。除此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金融创新”让银行完全失去了对发放贷款所带来的道德风险的顾虑。而这些金融创新的出现正是因为贷款总量的快速上升导致信贷需求转向监管成熟渠道之外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讨论次贷危机中两个最关键的工具:贷款证券化和信用违约互换(CDS),以及两家分别叫做房利美 (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 的住房抵押贷款公司。
贷款证券化
在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中,有一个片段描绘的是Steve Carell所扮演的Mark Baum一行人前往佛罗里达调查当地的房地产泡沫情况,在和一个脱衣舞娘对话中发现对方不仅在无固定收入的情况下申请到了房屋抵押贷款,而且还贷款买了整整五套房。
类似于大空头里这个令人惊奇的片段所描述的情况,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像这类次级贷款则被称为Ninja loan (No Income, No Job, No Assets), 简单来讲如此动一下手申请即批的三无贷款, 在抵押贷款市场中却占据了很大的份额。而抵押贷款机构(或者银行)没有任何动力去考核借款人实际偿还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发放的贷款被打包成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 Morgatage Backed Securities)的形式转手卖给了投行和其他投资者。各式各样的抵押贷款被打包进入一个贷款池,银行不再负责收债,而是整个贷款池的还款收入所组成的现金流被直接分配给了MBS的持有者。对抵押贷款机构来说,因为贷款即使违约了也是其他人来接盘,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借出去的钱能不能被还上。
MBS评级机制——没有任何人关心钱到底借给了谁
但次级贷款无论再怎么打包也不会消失不见,那么为什么投资者会对风险视而不见去接盘这些次级贷款所组成的MBS呢?这是因为抵押贷款机构在打包的时候进行了分级处理,从而把高风险的债务转换成了“安全”的证券:首先大部分是非常安全的AAA级证券,然后是AA级证券,BBB级证券,越往后规模越小但风险和收益越高,一旦贷款池中有出现违约情况,投资者的损失也是先由评级低规模小的证券开始承担,到最后才是占大头的高评级证券。
乍一看这种评级机制非常安全,但这种安全性成立的前提是评分本身是合理且符合现实的。而在次贷危机中,评级机制最大的问题是评级本身就有问题,大量垃圾次贷组成的证券被评级机构评为安全的AAA级证券[4]。这就好比一直买着安全的食用油,直到有一天中毒了才发现里面一半都是煤油一样。在次贷危机中,贷款证券化为次贷的爆炸性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信贷来源,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关心钱到底借给了谁。
信用违约互换 (Credit Default Swap)
在次贷危机中,房地产市场对资金的狂热需求使规模巨大且不受监管的金融衍生品迅速发展壮大。而在诸多金融衍生品中,对推动危机起到最关键作用的一类合约是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主要的作用是为投资者做债务违约的风险对冲[1:5]。简单地说,这类似于针对交通事故所出售的车险,CDS是针对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的金融合约。无论是贷款人还是其他投机者,都可以购买CDS。一旦借款人违约,就可以通过CDS获得赔付,而在平时只定期支付保费。然而,次贷危机中的问题在于,大量机构严重低估了房贷出现大规模违约的可能性,进而导致在出售大量CDS的同时却没有足够的准备金和风险对冲措施。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美国国际集团(AIG,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都在次贷危机中出售了大量CDS,美国国际集团因为没有足够的准备金来赔付大量的违约抵押贷款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的接管,而雷曼兄弟的CDS则是引发了另一个故事。
房利美和房地美 ——Too Big to Fail
除了MBS和CDS这样的金融工具,有两家企业在贷款证券化和泡沫的扩大化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其风险的恶化和隐含的政治权力紧密结合。这两家就是房利美(Fannie Mae) 和房地美(Freddie Mac)。房利美和房地美主要做的事情是购买贷款机构发放的抵押贷款,然后打包成MBS卖给投资者。同样含有高违约风险的次级贷款,但房利美和房地美和其他出售MBS的金融机构不一样,这两家企业发行的MBS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投资者是有政府的隐含担保的,因为房利美和房地美是为了维持抵押贷款市场稳定性而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特许企业。讽刺的是,正是有着这种未成真的隐含担保,房地美和房利美发现自己发行的MBS越多,反而越具有“系统重要性”,也就意味着政府的隐形担保越有可能成为现实。“政府担保(隐性或明确)的政治力量使得高风险资产看起来比实际更安全。这鼓励投资者加大杠杆,从而推动坏账增长”[1:6]。我们会在次贷危机中的救市过程中看到类似逻辑的产物屡屡出现,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 “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
2008:泡沫的破裂
2004年,过热的经济使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逐步加息,随之而来的就是抵押贷款利率的不断攀升。不同于过往,次贷危机中特殊的一个现象是被广泛运用的浮动利率贷款,很多不具备还款能力的借款人在低利率时借入房贷,而随着利率的升高与房价的下跌,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也迅速升高。加息成为了引发泡沫破裂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而之前所有推动泡沫的自我强化因素,也逐渐演变成螺旋下降的驱动因素。
贝尔斯登的挑战
与在同年9月破产的雷曼兄弟不同,次贷危机中最先倒下的主要投行是贝尔斯登(Bear Stearns)。虽然贝尔斯登的规模是主要投行里最小的,但是政府在救助时面临的困境却一点也不小。笔者将通过阐述贝尔斯登所采用的高杠杆策略以及救助时的挑战,来说明次贷危机中令政府决策者头疼的系统性风险问题。
CDO (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s - 担保债务凭证)
如同过度包装的礼品,CDO则是被层层打包的债务。前文提到,抵押贷款可以被打包成MBS, 而CDO等于是在MBS的基础上又打了一层包。CDO还可以基于其他CDO打包,这种由CDO组成的CDO被称为为CDO Square。而当底层的次贷违约率开始大规模上升时,一切基于上面的赌注就会带来大规模的亏损。下面的视频片段是行为经济学家塞勒(Richard Thaler)在电影《大空头》中用二十一点里的赌注解释Synthetic CDO背后的逻辑。
贝尔斯登在次贷危机中遭遇巨大亏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其持有了大量与次贷相关的CDO (担保债务凭证)。这不仅仅是持有大量CDO所面临的亏损风险,更在于其庞大的交易体系所隐含的系统性风险:“贝尔斯登有近400家子公司,拥有5000个交易对手和75万个开放性衍生品合约”[1:7]。一旦贝尔斯登崩溃,与其有交易往来的对手(几乎所有的主要金融公司)都会面临巨大的亏损风险,从而导致信贷渠道的崩溃。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意识到贝尔斯登倒闭可能引发金融体系的连锁崩溃,决定尽快救助这家随时可能倒闭的投行。
《 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 of 1913)》与 “用途转换”
在行政权力存在限制与约束的体系内,即使面对严重流动性危机和系统性风险并存的金融危机时,政府的干预仍然会面临诸多的非经济性阻力,而在次贷危机中,美联储与财政部面对的一大阻力就是其操作权限被现有法律规则所约束。面对贝尔斯登的烂摊子,最令伯南克和保尔森头疼的是,《联邦储备法》允许美联储向银行机构提供贷款,但不能向投行这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直接提供资金。和能救但不去救不一样,次贷危机中更多的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限制而救不了。
当然,决策者在联邦储备法中发现了创新的空间:1930年代大萧条时通过的《联邦紧急救助和建设法(Emergency Relief and Construction Act)》为《联邦储备法》留下了诠释空间,也就是允许美联储在“不同寻常且紧急(unusual and exigent circumstances)”的情况下,可以向非银行机构提供贷款。利用该条款所赋予的空间,美联储宣布提供约2000亿美元的资金,允许投行等金融机构用次贷证券等高风险资产做抵押来借入资金以缓解流动性危机。
一些学者的将类似这样对原有法律和规则进行灵活解释并扩展其定义来干预危机的方式称为“用途转换(Conversion)”[3:1]。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规范下的共识,基于的是政府对市场的最小干预原则。决策者想要通过完全的改革获得授权来应对危机一定会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而金融危机又非常考验决策者的反应速度,所以在这样的限制下最容易获得授权的方式就变成了对原有法律条案基于现实中的困难进行“再转换”。
收购
“3月4日,在向贝尔斯登提供隔夜贷款时,回购市场的贷款人甚至拒绝接受美债作为抵押品”[1:8]
投资者并不相信美联储所能提供的资金可以填补贝尔斯登的全部窟窿,这导致美联储提供的庞大的紧急流动性后并没能让贝尔斯登起死回生。贝尔斯登这类投行非常依赖以短期借款来持有长期非流动性资产,一旦投资者认为其基本面无法挽回,金融机构很容易因为投资者的迅速撤资从而陷入流动性危机。
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可以将贝尔斯登所有亏损和潜在漏洞全部接盘的实体出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受法律的限制,财政部无法直接为贝尔斯登兜底,所以只能从私营部门中找一个可以收购贝尔斯登的机构[1:9]。为可想而知,这一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其他金融机构并不愿意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承担极大的风险来接手难以预估的亏损漏洞;而另一面,政府也很难在整个系统还没有到最坏的情况下,承受运用纳税人资金去解救某一家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压力。最后,贝尔斯登的清算银行,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在美联储承诺提供300亿美元贷款来承担贝尔斯登投资组合的未来亏损后接盘。
2008/07-2008/09: 政治体制内的阻力
在救助贝尔斯登中,决策者主要是以寻找既有法律条文中的空间来获取干预的权力,避免了进行全新的改革和立法。然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决策者在现有法律框架上找到诠释的空间。下面,我们通过政府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救助过程来探讨为何后者在权力存在制衡的体系下是困难的。
贝尔斯登遭遇危机后,比贝尔斯登规模大20倍不止的房利美和房地美也是岌岌可危。用保尔森的话来说,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一场“等待爆发的灾难”[1:10]。早已看到这两家公司的风险的保尔森本想趁贝尔斯登问题被解决的时机推动国会通过《住房和经济复苏法案(Housing and Economic Recovery Act of 2008)》来明确干预的权力,但此时法案在参议院被否决[1:11]。
对此,达利欧的解释是,政治体制内的共识很难在没有在最坏情况发生前轻易达成:“决策者则在政治体系内运作,他们必须要达成成普遍共识,直到各方都认为问题无法容忍时才会采取行动。”[1:12]。除了缺乏共识,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还面临一种特殊的阻力。保尔森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房利美和房地美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只要一说他们有任何问题,他们就会安排财政部接收4万封邮件,解释他们获得全部授权以完成重要工作有多重要…如果想找它们的麻烦,它们会安排一批市长给你打电话”[1:13]。最终,在一系列博弈后,财政部在7月底说服立法者通过了《住房和经济复苏法》,给予财政部范围广泛的紧急权力来注资房地美和房利美。保尔森描述到“如果国会未能批准,市场就会崩溃。赌注是巨大的”[1:14]。通过该法案所新成立的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于9月7日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
2008/9:雷曼兄弟的倒闭与市场崩溃
2008年9月14日,在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的前一天,同样遭受巨额亏损的另一家主要投行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收购。在这里笔者会通过总结书中内容的方式来回答两个问题:雷曼兄弟为什么没能被其他机构所收购;为什么它的破产在金融市场引发了雪崩一样的效果?
为什么没能像贝尔斯登一样被收购
救助雷曼兄弟有着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上的双重阻力。经济上,雷曼兄弟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大到没有人能准确预估出背后的财务漏洞有多大。面对雷曼兄弟这种资产负债表远大于贝尔斯登的公司,所有的潜在买家都无法承担可能隐含的风险,并不愿意在没有政府担保的前提下进行收购。因难以确定需要提供多少流动性来承担收购雷曼资产的隐含风险,美联储也无法提供贷款。即使决策者在《联邦储备法》第13(3)条上找到了可以为投行注资的诠释空间,但其规定了美联储的贷款必须有合理偿付的可能,而雷曼兄弟像黑洞一样的资产负债表显然不符合这一标准。
此外,在接连救助了贝尔斯登、房利美和房地美后,决策者还面临着政治层面上新的阻力:救市所带来的公众压力和道德风险。美国民众尤其对于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投行愈发感到不满。与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来稳定房贷市场不同,公众很难将救助投行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联系到一起。更多的人希望看到金融机构得到惩罚,甚至一部分政府官员也主张应该让雷曼兄弟倒闭作为对其他金融机构的警示,避免使金融机构产生政府会介入的预期从而助长其冒险行为。雷曼兄弟的困境在决策者眼中是大而不能倒,而在公众眼里却是罪有应得。
Jeffrey Chwieroth和Andrew Walter对这样的公众心理有着更深层次的解释:新自由主义为选民提供了一种原则性的反对立场,那就是反对对某一特定群体或阶层给予特殊待遇,并且政策要优先考虑纳税人的利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原则是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进行供给侧干预,而这一原则对不管左翼还是右翼选民来讲,都对反对政府救助“低效且不公平”的大型机构的立场提供了理由[3:2]。次年发生的AIG奖金事件[5]正好印证了公众对此类特殊待遇的强烈反感,并且这种立场不会因为危机的缓解而消失。
雪崩式的自我强化
In a crisis, where fear is governing, a financial failure of even a medium-sized bank can cause havoc(在一场由恐惧支配的危机中,一家中型银行的破产都可以带来毁灭性后果)[2:1]
次贷危机展示了信心的崩塌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向全球金融系统扩散的,而雷曼兄弟在衍生品市场的深度参与则是整个金融体系连锁崩溃的起点。相比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出售了规模更为巨大的的CDS,破产时市场预估其CDS风险敞口达到了4-6万亿美元。引发恐慌的核心原因在于,由于CDS市场缺乏透明性,在与房屋抵押贷款相关的债务工具(如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已经开始出现大规模违约的情况下,市场无法判断哪些交易对手持有这些高风险CDS,也就意味着有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可能因此面临巨大的风险敞口而无法对冲。这种对这整个金融体系安全性的高度不确定迅速转化成恐慌,并通过金融系统的关联性向外扩散。
主要储备基金(Primary Reserve Fund)作为货币基金被冲击的典型案例就很好地展现了一个机构的风险是如何在一个高度关联系统内快速蔓延到其他领域的。货币基金对于当时很多的普通投资者都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选择,有着很强的灵活性却通常比银行存款的收益高。但更高的收益通常伴随着更高的风险,货币基金投资主要集中于诸如商业票据,政府债券等低风险的短期债务工具,然而,当这些“低风险”的投资发生违约时,风险会迅速传导成灾难。这是因为低风险所预设的逻辑一旦被打破,恐慌和崩溃的速度通常只会比风险累积的速度更快,带来更大的破坏性。主要储备基金持有了大量雷曼兄弟发行的短期商业票据,随着雷曼的破产,这些不可能会被兑付的票据瞬间变成了废纸。在雷曼兄弟破产的第二天,主要储备基金净值跌破1美元,陷入挤兑危机。主要储备基金的破位引发了货币基金赎回潮,投资者担心自己持有的货币基金也有可能面临与主要储备基金类似的风险而破位。赎回潮是灾难性的,因为货币基金作为企业短期融资的关键来源,其投资大多是企业日常流动性所依赖的短期商业票据。赎回潮使流动性危机迅速蔓延至各行各业: 通用电气、可口可乐等企业都开始遇到延期或者出售商业票据的困难并面临短期资金缺口。
达利欧指出,“雷曼兄弟的倒闭尤其可怕,因为它与金融系统的其他机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但认知不足的关联”[1:15],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市场陷入恐慌,恐慌使投资者们尽一切努力将资金转向安全的资产,而这种行为反过来更加剧了流动性危机,使金融市场陷入恶性循环。随着恐慌蔓延,资产价格持续下跌,赎回和抛售不断加剧,整个金融体系进入一种雪崩式的自我强化之中。
资料注:2008年9月24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在雷曼兄弟破产后的全国讲话中阐述了次贷危机发生的大致原因与过程
柠檬社会主义 - Socialism for the rich; Capitalism for the rest
“柠檬社会主义”一词是经济学家克鲁曼(Paul Krugman)在2008年用来形容美国政府在次贷危机中所采取的干预手段,有些学者也称其为危机社会主义,包括了一系列在次贷危机救市中耳熟能详的法案和措施:财政部主导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 TARP),《 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由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等等。柠檬社会主义这个词的产生,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嘲讽意味的,主要是用来批判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大型企业的举动,而这相当于企业失败的后果由普通纳税人承担。就像联邦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抨击救市方案时所说的,“富人的社会主义,穷人的资本主义(Socialism for the rich and free enterprise for the poor)”。整个救市举措在当时以及现在都具有极大争议性,而争议性主要来源于它所隐含的道德风险。然而,在整个信贷市场已经陷入崩溃边缘的2008年9月,现有框架能提供给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权力已经远远不足以挽救接近枯竭的流动性,大规模的救市方案成为了必要的举措。TARP的通过和实施成为挽救陷入困境的市场的重要的举措之一。“解决偿付能力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提供更多的股权资本”[1:16],所有后续的纾困方案几乎都围绕这一原则以缓解市场信心崩溃的根源性问题。
TARP和2008大选
在雷曼兄弟破产前的救市尝试中,美联储通过《联邦储备法》13(3)所能提供紧急贷款的范围和权力还可以挽救个别陷入危机的企业,但在雷曼兄弟破产后,接近冻结的金融市场所需要的已经不只是短期上的流动性支持,而是直接的资本注入以恢复偿付能力。然而,决策者无法救助雷曼兄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联邦储备法限制了美联储所能提供的贷款规模,而TARP则会直接给予财政部权力来运用财政手段购买不良资产并注资金融机构。保尔森所推出的TARP,核心是计划筹集7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这一救助方案的实施,但像TARP这样的财政手段所需要的资金实际上通过联邦政府发行债券来筹集,这笔天价资金的要求自然在国会遭遇了巨大的政治阻力。
TARP的政治阻力主要来源于其所面临的公众反对压力。次贷危机中面临危机且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主要是大型金融机构,然而和在救助雷曼兄弟所面临的困境相似,公众对政府的救助计划是持有普遍且强烈的反感的。 一方面,普通民众很难将救助金融机构的利益和自身利益联系起来,也对大型金融机构这一特定群体进行救助感到不公。另一方面,面对糟糕的经济情况,惩罚这些被视为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的呼声也在日益增加。
“We Americans don’t like bailouts. We think if you make money taking risk, that’s great, but if you lose money, the government shouldn’t be the one that comes in(我们美国人不兴救助。我们认为,如果你冒险赚到了钱,那很好,但如果你赔钱,政府则不应该介入)”[2:2]
保尔森的这段话反映了美国公众的普遍情绪,在他已经从财政部离任的2009年,民意调查依旧显示90%的美国民众反对TARP[2:3]。这般民意的不满直接导致TARP在国会遇到两党阻力,甚至在共和党内部都面临着极大的阻力—救市并不符合保守派共和党人对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与政府职责上的观念,即反对政府运用过多的权力干预市场。即使相当数量的共和党人已经相信TARP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政治理念上的直接冲突依然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如何向自己的选民解释这一与其从政理念相反的决定[2:4]。TARP的推出时间恰恰赶上了一个月后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民主党也不想看到共和党在大选前取得重大立法上的胜利[1:17]。保尔森在自己的访谈中曾经提到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最初是表示支持TARP的,但其前提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也支持TARP,因为公众的呼声一定会让反对TARP在政治上更受欢迎。万幸的是TARP (H.R.1424)在经过两党多次谈判,修订并增加诸多监管条例后在国会最终获得通过,并被时任总统小布什签署成为法案,这给予了财政部亟需的授权。
争议
对于TARP在实施过程中的主要争议,下面将从核心的争议点中分析反对情绪的来源以及相应回应。
对救市本身的反对
第一个争议点是反对救市整体政策的呼声。这样的情绪不仅源于保尔森所提到的“美国人不喜欢救市”的文化传统,还受到了小政府理念和对纳税资金用途偏好的影响。公众更希望政府可以让这些被视为一手酿成这场灾难的金融机构自行倒闭从而接受惩罚。在某种程度上,这恰恰是因为公众很难将救助金融机构防止其崩溃的系统性意义和自身的短期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达利欧则是通过80年前的大萧条的历史过程来反驳这一观点[1:18]。大萧条所造成的极大破坏力并不是源于经济问题上的严重性,而恰恰是因为市场没有能得到及时的救助,相比之下,现代金融体系的依赖性和复杂性远远高于大萧条时期。
区分健康与不健康的机构
TARP的第二个争议点是救助计划是否应该区分健康的金融机构和资不抵债的的问题机构,而救助资金并不应该流向后者。达利欧认为,以雷曼兄弟破产后的危急情况,决策者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分清哪些机构是健康的,哪些机构是不健康的,而且在不透明的市场中下搞清楚一家机构是否健康本身就不现实[1:19]。保尔森则认为,即便公众难以接受对问题机构的注资,与直觉相反,对整个金融系统不加区分地支持在经济上通常是更有效的(unusually effective)。与只对个别问题银行进行救助的欧洲国家相反,TARP在更快速地恢复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性与流动性[2:5]。
对被救助机构的监管
最后一个主要争论点是是否应对接受救助的银行进行严格监管,强化监管的呼声在AIG奖金门事件[5:1]后更加强烈。但TARP与全面国有化的区别是,TARP只是通过注资恢复市场流动性,所以对发奖金这样企业内部的运营管理的控制是十分有限的。保尔森认为在救助条款上增加严格的条件将直接导致金融机构不愿意接受TARP的资金,“They would all be saying we’re “healthy,” right up until they failed.(金融机构都会说自己是健康的,直到在崩溃的边缘下坚持到破产为止)[2:6]”,这正是决策者想要去避免的情况。将TARP的救助方案设计为自愿性质,就是希望金融机构能在面临崩溃前主动接受资金注入,从而避免整个金融系统遭受更大的灾难。
TARP无可否认引发了大量的道德争议,但从经济结果上来看,其最终在仅使用了约4300亿美元(原计划为7000亿美元)的前提下,不仅提前将放出的资金全部收回,还为美国财政部带来了近500亿美元的利润[1:20]。
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
TARP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短期信心崩溃和恐慌问题,但是长期的信心却依旧难以恢复。这是因为整个市场还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个人,都倾向于持有安全资产,对风险格外敏感。而这样的后果则是信贷的持续萎缩,以及伴随而来的整体的经济停滞。
“11月发布的大多数重要经济数据比已经非常糟糕的预期更糟。消费者支出迅速下降…各个行业的企业都因盈利不佳而进行历史性裁员”[1:21]。
通常来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降低利率刺激信贷活动,但当利率已经没有下降的空间时,这种方法就会失去效用。在这种背景下,量化宽松应运而生, 并在次贷危机中被美联储首次使用。其应用的基础在于,即使短期流动性问题得到缓解,银行可能仍因风险厌恶而不愿发放信贷,但当有远超其所实际需的额外流动性注入时,银行很可能会逆转其风险厌恶的行为,从而激活信贷市场。作为非常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的核心目的是在传统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继续起到刺激信贷从而恢复经济活力的作用。在几年前的新冠疫情中,美联储在相似的条件下(疫情引发的萧条叠加疫情前利率水平已经处于低位)实施了第四轮量化宽松。
那么量化宽松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与TARP这种财政政策所依赖的政府预算不同,量化宽松的钱基本上是美联储通过“印钱”来提供。以2008年11月启动的第一轮量化宽松为例,美联储“印”了6000亿美元用于购买房利美,房利美等机构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目的则是为住房贷款市场注入超额流动性来降低贷款利率,从而打破信贷不断萎缩的螺旋。量化宽松创造出来的资金也可以用来购买国债,政府债等其他资产,取决于决策者想让这些超额流动性流向哪里。
理解量化宽松的操作大概后,一个常见的担忧就是凭空印大量的钱会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胀,但这一情况在次贷危机中其实并未出现,而原因在于印钱所产生的通胀压力被信贷萎缩和萧条所导致的过剩产能抵消了。正如达利欧所指出,“通货再膨胀不一定导致通胀,可能只会抵消通缩,具体取决于政策力度和资金流向”[1:22]。 美国的通胀压力在次贷危机后接近7年的低利率背景下都保持较低水平,关键因素在于萧条造成的过剩产能,而这些过剩的产能直到次贷危机发生的8年后才被完全消化[1:23]。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Act of 2010)
对TARP的一个主要批评是政府对“大而不能倒”机构的救助很可能会使更多的金融机构在未来利用这种的系统重要性迫使政府为不良经营买单,从而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国会两党在危机后达成了共识,并采取行动,大幅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Dodd-Frank Act在2010年应运而生并被通过成为法律。Dodd-Frank Act加入了大量针对‘大而不能倒’机构以及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目的则在于避免类似次贷危机中无监管所导致的泡沫累积情况再次发生。
然而,严格监管与避免危机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有学者指出了两者之间的悖论:中产阶级财富资产的日益金融化,使其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产生了高度依赖。这种依赖使得政府在危机中几乎无法回避救市这个选项,因为保障金融稳定也意味着保护拥有重要政治地位的中产阶级的财富。而正是这样巧妙的关系,使得即使有重重限制,决策者依旧会想办法找到空间来绕开限制去推动救助政策。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新冠疫情下的救市操作。为了避免无限制的大规模救市再次发生,Dodd-Frank Act在法律上限制了美联储和财政部的行政裁量权,但在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与财政部依然可以绕过其中的限制,重启了次贷危机中使用的紧急贷款工具,这证明再严格的监管改革也很难阻止政府在危机时的直接干预[3:3]。
严格的监管无法抵挡现代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所带来的必然危机。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保尔森认为,监管改革的核心并不在于增加数量或制定更严苛的规定,而是构建更“有效的”监管机制。他认为次贷危机前美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是“不足,过时,陈旧且缺少必要权力的(inadequate, outdated, outmoded, without the necessary powers)” ,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应当可以良好地解决这些弊病。保尔森反对过度监管的核心理由则在于,试图消除金融系统里所有风险只会迫使风险转移到不透明或监管不足的领域,反而会加剧整体的系统性风险,而一个真正有效的监管机制并不会执着于将所有的风险清零[2:7]。
达利欧则认为,Dodd-Frank Act等危机后的监管改革有着一种人性驱动的周期性规律与限制:人们对于灾难的记忆是会逐渐淡化的。他写道,“随着灾难性影响的逐步消退,欣欣向荣的景象再度出现,而法律越来越受到轻视,新形式的实体创造出新形式的杠杆化工具,将带来以同样的方式演变发展的新一轮债务危机。”[1:24]
参考文献
瑞·达利欧(Ray Dalio). 《债务危机》. 译者:赵灿/熊建伟/刘波 中信出版社, 2019-3, 引文分别来自第182, 185, 186, 208, 209, 212, 214, 216, 221, 222, 223, 225, 228, 230, 240, 248, 250, 266, 268, 273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ller Center. “Henry Paulson Oral History.” Presidential Oral Historie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n.d., Link. ↩︎ ↩︎ ↩︎ ↩︎ ↩︎ ↩︎ ↩︎ ↩︎
Chwieroth, J. M., & Walter, A. (2021). Neoliberalism and banking crisis bailouts: Distant enemies or warring neighbo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100(3), 600–615. Link ↩︎ ↩︎ ↩︎ ↩︎
Ashcraft, A. B., & Schuermann, T. (2008). Understanding the Securitization of Subprime Mortgage Credit (Staff Report No. 318).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Link ↩︎
Wikipedia contributors. “AIG Bonus Payments Controversy.”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n.d., Link ↩︎ ↩︎